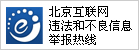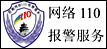教育惩戒权如何实施才有效
教育惩戒权如何实施才有效
导读:近段时间以来,教育领域出现多起教师惩戒失当的案例,如陕西一教师长期辱骂学生、山东一教师用课本抽打逃课学生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是否有必要通过立法形式明确赋予教师惩戒权?惩戒权应该如何行使才能既确保教师履行教育管理职责,又维护学生身心健康?本期“声音版”邀请相关专家、教师、学生及家长一道进行探讨,敬请读者关注。
学者声音
以法治思维看待惩戒权入法呼声
□ 靳澜涛
伴随着教师法修订工作的日趋深入,许多具体的制度设计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重点。其中,“惩戒权入法”的呼声此起彼伏,明确赋予教师惩戒权似乎已势在必行。
惩戒,是学校以及教师维护正常校风校纪和确保教育管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主要目的是用以纠正学生的失范行为,实现育人目标,其在本质上同激励、表扬、说教等方式是一样的。对“要不要惩戒权”的回应似乎并无过多理论障碍。真正的难点和争议点在于:作为应然权利和默示权利的惩戒权是否需要明确入法,是否可以将其直接纳入教师法关于教师权利的规定,以及哪些行为需要惩戒,怎么实施惩戒,根据什么惩戒,等等。
面对实践中教师不敢管、不能管、不想管或者过度惩戒,乃至体罚等现实问题,惩戒权的明确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确实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然而,是否将其纳入本次教师法的修订内容,特别是作为一项明示的教师权利予以列举,仍然需要仔细拿捏。只有慎重考虑其入法的必要性、可行性、条文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落实中的可操作性,才能做到科学立法。
第一,教师法尚未明确规定教师惩戒权,并不是对实践中惩戒行为的全盘否定。惩戒,是教师进行教学管理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具有附属性和工具性,并非一项独立的权能,其最终指向仍然是教书育人之目的。目前,教师法第7条已经明确规定,教师享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等权利。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来看,惩戒权是教师实现教育教学权和指导评价权的必要与合适的手段,其通过法律解释和逻辑推理,完全可以得到立法的肯认,并将在个案中接受比例原则的严格审查。因此,针对教师惩戒权,所谓立法缺位和实践失范的理论质疑本就需要理性认识。在“惩戒权入法”的社会呼声之下,应当跳出立法中心主义的窠臼,深刻认识到惩戒权与教育教学权、指导评价权之间的层次性和包含性,并充分重视法律原则尤其是比例原则的适用空间。
第二,惩戒权的赋予主要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主体上具有特定性。无论是山东青岛出台的《中小学校管理办法》,还是广东省司法厅公布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送审稿),抑或中央层面最新出台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这些地方立法或者中央政策文件虽然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教师惩戒权”这一概念,但均将权利主体限定于中小学教师,权利行使的对象主要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不同学段教师的权利与义务不尽相同,亟须立法予以类型化规范。但是,从实然角度来看,时下的教师法作为教师行业的基本法,其权利义务的规定应该着眼于整个教师职业的共性特征,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学段的教师。因此,将惩戒权的行使条件、实施方式、范围限度、不法后果、救济途径等问题交由具体的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来明确,似乎更为妥当,如此既有助于推进惩戒行为的规范化与法治化,也确保了法律条文的自洽性以及不同立法之间的衔接性。
第三,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均禁止体罚与变相体罚,但是鲜有立法条文进一步明确规定何为体罚与变相体罚。如果教师法正式载入教师惩戒权,社会公众会渐次叩问:什么是惩戒权,它的边界在哪里,内容和形式又是什么,哪些行为不属于教育惩戒的范畴,惩戒与体罚、变相体罚如何区分,这些都是较为棘手的理论问题,学界尚未形成共识,现有立法也语焉不详。如果抛开这些争议问题,只是模糊地将“批评教育或适当惩戒”作为教师权利之一,必将面临立法语言的精准度质疑和现实中的权利滥用问题。况且,在实践中,学生及其监护人对体罚与变相体罚的理解往往趋于泛化,教师过去经常使用的罚站、罚作业等惩戒手段不时被认为是体罚或变相体罚,对学生的训诫也有可能被贴上“侮辱人格尊严”的标签。如果明确赋予教师以惩戒权,却又漠视其行使范围和实施强度,显然缺乏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必将使得教师惩戒权的运用更加形骸化,由此产生的矛盾纠纷不容小觑。对于多数教师而言,仍然会基于尺度的拿捏不准而不敢举起“戒尺”。
中国观察
国际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