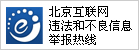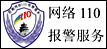身在画中 活在边缘
身在画中 活在边缘




着火的船桨。受访者供图
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25年后,刘声还是个“不出名”的画家。他只有一次在公众场合登台的经历;网上对他的报道一只手数得过来;他的工作室从广州市大沙村搬到金沙湾,再从金沙湾搬到西三村,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
他的画笔也都在边缘打转,画中的人有理平头斜眼打电话,从脸到腰黑得像炭的包工头;有穿着雨靴赤膊上阵肌肉紧绷的农民工;也有一群围观拆迁面色沉重的村民。他们是劳动人民,也是一群要辛苦“揾食”(广东方言,指谋生很难——记者注)的人。
有时候,刘声看上去和画里的人相差无几,他不高,平头,黑皮肤,T恤牛仔裤套件冲锋衣,不止一个人说过,他像个包工头。
因为想要弄懂“人在遭遇环境改变时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逻辑”,他拿着相机走在一个个城中村,那些影像最终被他的画笔定格成一幅幅水彩画。
高耸的水泥桥下,农民在水面上孤零零地撑着木板;交叠的木材上,看不见脸的民工枕着手臂侧卧着睡了,扭曲的后背打了几个结;或者干脆是一堆被塑料胶带缠绕的泡沫盒子,水渗到地面,再流到一堆五颜六色的垃圾袋上……
像很多画家一样,他也关注过那些充满“装饰性”的东西,但创作一直断断续续。他跟着美院的老师去陕西写生,盯着人文建筑和山水风景,“就是不快活”。可一闻见水产市场的腥味儿,看到工人光着膀子的肌肉线条,他整个人立马打起十二分精神。
他的画里出现过一个面部黝黑的男人,挺着肚腩,兀自站在横七竖八的水泥石块上望着远方,脸上挂着的一抹红说不清是突起的筋结还是挣扎后的血迹,下半身被残破的水泥柱子替代。
那是他从村民口中听说的钉子户,因为“硬扛”,那栋楼头顶着高速公路大桥耸立了10年。
“经济发展了,城市向乡村扩张,拆楼、建楼是前几年最有代表性的冲突。”刘声指着画说。
比他小几岁的房东也被塞进了画里。大水漫过膝盖,他就那么伫立着,脸上没有表情,背上是一整棵被水冲烂了的芭蕉。
房东从小跟着父亲种芭蕉。赶上房地产崛起,高楼大厦入侵,珠三角的地价陡涨,他租不起本地农田,干脆找上几个哥们儿,跑去粤西包下了100亩耕地。
这片芭蕉地遭遇过台风“山竹”的侵袭,损失惨重;还有一次被水淹,他趴在泡沫板上拼尽全力才游出来。
“丰收价格就低,遇上自然灾害反而高,可那时候他也没货。定价的话语权不在他们手上,到现在还是靠天吃饭。”刘声叹气,他听说房东的祖辈就是流浪到西三村安家种田,因为时代环境变化,现在他又不得不外出流浪。
“人生活在一层层的网中,因此很多人不愿表达,他们真正的生活没被看见。”刘声认为,这些小人物才是中国的大部分,他们背后的问题复杂又普遍,“有时代共性,有大把机会,也有对改变命运的期待。”
画下这些作品时,刘声的耳畔常常伴着打桩又拆掉的“咚咚声”。2016年,他搬来西三村,画室是个种着两棵树的小院子,被一幢拆迁楼堵着。
这是广州番禺区的南浦岛西北角,一条高速公路横穿过去,把村子割成两部分。拆了建、建了拆的乡村在这头,另一边曾经的江边耕地已经成为整个半岛最贵的高档小区,人流熙熙攘攘。
在夜晚,车辆在变动的光线里飞速穿梭,远处的“广州圆”时隐时现,闪着“欢迎投资”的字样。刘声举起手机,常常能拍到四五种元素同框的画面。
在西三村走上一圈,绕不开破败的房屋,木头和碎石块乱七八糟地堆在路两旁。几乎每过两三个月,都会冒出一座新楼,建筑物时刻在新建,也有可能会烂尾。
新开发的楼盘和高速公路逐渐取代了传统农田,宅基地成了村民依赖的重心——他们不断盖房子,然后再出租,把一楼给别人做仓库,楼上就打上隔断专供外来打工者居住。周边村子“淘汰掉”的服装小作坊一股脑儿搬来,一个月里,房子全部被租光,租金还一下涨了2~3倍。
“城市的冲撞让这个处于边缘的村落被夹在中间,只能跑步前进。”他说。
这个画家“不想沉迷在艺术圈内部”,为了还原村民活生生的遭遇,他决心进入现场。
中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