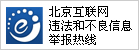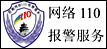网络化时代社交文化的社会伦理
社交网络的发展为人们获取信息、分享生活、获得社会资本等提供了便利,但是其内在附着的伦理问题也应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因为,在个体化特征之外,人对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促使其不断走向联合体,通过交往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形成集体生活以抵御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
伴随社会生活的网络化进程,社交网络成为个人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个人使用社交网络具有多种目的:休闲、维持现有社会关系、建立新社会连接、紧追时代潮流,抑或获取社会信息等。随着社交网络用户的增长,探讨社交文化对社会关系、社会目标和社会行动的潜在影响,显得尤为关键而重要。
社交网络是个人通过电脑或手机等移动设备相互交流和分享信息的网络平台,支持用户基于不同场景的沟通、分享、服务和娱乐的需求。尽管各类社交网络内部文化差异巨大,但总体而言,各类社交网站均允许用户在平台内以文本、图片或视频的分享,创建一个公开或半公开自身的状态,并通过相关应用和链接与其他使用者进行沟通和交流。
因此,社交网络不仅是一个复制现实人际交往的平台,而且还是一个人际关系再造的信息互动平台。为了增加自身的标识性,人们不断在社交网络发表新鲜事、更新状态,分享着自己的心情、行为、位置,乃至一切私密话题。正如熊培云所言,社交网络使社会从原先单向透明的权力国家过渡到全景透明的网络社会。在这样一种全景式网络社会中,人们不仅是信息的分享者,同时也是他人分享信息的窥视者。信息生产与信息监视成为同步交织的个人网络行为,创造出一种新形态的网络文化生态——窥探文化。加拿大传播学者尼兹维奇(Niedzviecki)将“窥探文化”的本质概括为“过度分享”,即个人将私密的生活空间推向公共消费领域,无防备且高频率地分享自己真实生活和个人信息,通常(但并非永远)基于娱乐的目的,但往往以隐私为代价。
社交网络,作为一种市场产品,将用户生产和分享的信息作为核心功能,鼓励用户进行更多的信息分享和自我揭露,个人隐私信息成为社交网络可以进行交易的商品。随着社交网络与移动智能设备的结合,个人可以随时随地分享身边新鲜事,呈现即时化分享的特点,媒介更加多元化,内容更丰富。然而,社交网站即时分享中公私界限的模糊性以及社会互动的场景化,使个人在社交网络进行信息分享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个人隐私的关注,打破个人维持的日常生活中的隐私边界。随着社交网络的持续发展,社交用户网络分享行为不仅在数量上持续增长,而且以自我揭露娱乐化为特征的过度分享行为也越来越普遍。
因此,在社交网络中,隐私悖论一直存在,即在社交网络使用中,人们对隐私的态度和隐私保护行为具有非线性的相关性,人们对隐私信息的关注并不能减少人们在社交网络中自我暴露隐私信息的行为。
社交网络中的数字化伦理
新的网络技术正在重塑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以及自我表达的能力,对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社交网络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开始进入网络交往的新阶段,复制原有的社会关系并搭建新的社会关系。人们在社交网络中通过关注、点赞、评论、分享、转发等方式相互沟通,人际关系因此成为由好友数、粉丝量、关注度、评论和点赞量、转发率等数字化特征所表征的网络关系,但这种网络关系却使社会交往的情感价值被消解和庸俗化。媒介即信息,正如传播学者肖特(Short)等人论述的那样,传播媒介的不同特性会导致不同的心理和行为,面对面的视觉沟通更利于情感性的交流,而中介的言语交流则更利于任务性信息的传递。社交网络作为依托网络媒介进行情感性交流的重要工具,将人际交往具化为关注、点赞、转发、评论等数字化网络行为,弱化了情感性沟通,使社交呈现出形式化、肤浅化和广而不深的特点。话语的贫乏和缺失抽离了社会交往的内在情感性基础,使网络社交成为一种程式化的工具,在被点击中沦为数字化道德的符号。
除情感缺失之外,社交网络中的数字化特征使人们现实生活中社会关系的隐蔽性因社交网络而具有了可见性。人们在社交网络中不仅熟知自己的网络好友规模,还可以根据分组或标签功能对这些既有关系进行分类和管理。正如福柯指出的,“现代社会进入了一种中心化的观察系统之中,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最经常关注的原则。”当人际关系被置于一种公开的、可见的数字化状态中时,社交网络即成为人们自我展演的重要方式,正如媒介研究学者埃里森(Ellison)研究发现,个人在社交网络中的信息暴露与其在社交网络中好友数量之间存在正相关,而个人在社交网络中设置隐私限制的多少与他们通过社交网络认识新朋友的时间长短存在负相关。因此,可以看出,社交网络人际关系数字化的可见性正在让人们以个人的信息为代价,去实现社交网络提供的社会化和娱乐化功能。
中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