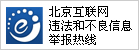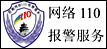构建信息科技伦理框架
几十年来,迅猛发展的信息科技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悄然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认知,如牛津大学数字伦理实验室主任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所言,“数字革命改变了人们对价值观、优先权、品行和可取创新的看法”。因此,无论是从物质还是精神层面出发,信息科技伦理都应竭力跟紧信息科技发展的步伐。
信息科技伦理框架现状
信息科技范围广泛,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量子信息等。全球主要国家对发展信息科技给予了足够重视,仅2018年以来,美国先后发布了《网络安全战略》《美国人工智能计划》《美国国家量子法案》等,欧盟制定了《网络安全法案》《量子技术旗舰规划》,韩国、印度启动了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新加坡制定了《网络安全法案》。我国的智能制造战略、“互联网+”行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在相关政策中都或多或少提及了伦理问题。
与平面化的伦理评价不同,立体化的伦理框架对于科技良性发展更具实效性。伦理框架是一套成型的、处于相互作用下的伦理规范的组合和运行机制。信息科技伦理框架的研究遵循经典伦理理论(如功利主义伦理学、义务论伦理学等)的范式,为不同的信息科技设定伦理框架。发源于医学伦理学的双重效应学说,近年来也被频繁作为人工智能伦理框架的理论基础。
当前,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是最受学界关注的信息科技。对于大数据研究面临的隐私和伦理挑战,苏黎世大学教授瓦耶纳(Effy Vayena)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者指出,新的伦理框架关心的不是数据是否应该用于研究,而是如何从尊重伦理和隐私的基本原则中获取利益。无独有偶,弗洛里迪团队在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白皮书(A White Paper on an Ethical Framework for a Good AI Society)中也指出,要抓住机遇,制定法律、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将获益建立在伦理框架的基础上。可见,伦理框架是信息科技良性发展的重要支撑。
目前,关于信息科技伦理框架的研究比较分化,几乎每一项信息科技中都能找到伦理框架的依附点。在“皮之不存”的依赖关系下,信息科技伦理框架确实应与信息科技保持高度一致,但这种一致并不意味着要“各个击破”。事实上,在每一列信息科技的列车上都装上伦理雷达既困难又阻力重重。因此,何不回归到框架的本义,圈定一个足够宽广又有边界的地域,让所有列车在一定期限内都不驶出界?这一思路指向建立信息科技的统一伦理框架。
构建统一伦理框架的可行性
欧盟近年制定了一些统一的针对新兴科技的法规,如European Group on Ethics in Science and New Technologies等,伦理框架虽然很难像法规那样实现大范围的统一,但在某一科技领域构建统一的伦理框架未尝不可。并且,具有整体主义文化传统的我国,对于构建统一的伦理框架有更深沃的土壤。
西方已有学者尝试提出整体的信息科技伦理框架。英国三方研究和咨询公司(Trilateral Research & Consulting)的赖特(David Wright)提出了一个可以对任何涉及信息技术的政策、服务、项目或方案进行评估的伦理框架,该框架使用比彻姆(Tom L. Beauchamp)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生命伦理四原则作为标准,并加入了隐私和数据保护的内容。这一伦理框架显得有些“野心勃勃”。统一的框架不是一定要将所有信息科技一股脑儿地包纳进来,它应该是这样一种框架——当它面对不同的信息科技时,能够通过自身简单的变化而变得继续适用。这样,框架本身的结构和开放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运行机制出发,可以将框架的基本要素分成主体、客体、标准、对象和程序,此前的伦理框架研究极为关注框架的程序,即对于框架的步骤和顺序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早期,如福克斯(Richard M. Fox)和迪马克(Joseph P. DeMarco)在《道德理性:应用伦理学的哲学进路》(Moral Reasoning: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 Applied Ethics)一书中提出了“建构一组问题”“收集资料”“探寻不同意见”“评估各种意见”“作出决定”“采取行动”六步骤。近年来,如曼海姆(Sara Mannheimer)等人在2017年国际数据监管大会(International Digital Curation Conference,IDCC)上提出的“STEP”框架,可以作为实现安全、伦理和使社会媒体数据研究可持续的重要“步骤”。
中国观察